发布日期:2026-01-02 浏览次数:
时时彩平台,腾讯分分彩,北京赛车,北京赛车pk10,北京赛车pk10技巧,幸运飞艇,彩票平台推荐,飞艇开奖,幸运飞艇官网,大发彩票,彩票平台推荐,500彩票,六合彩,大乐透,双色球,体彩足球,体育彩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从目前通用的来看,一般都把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之始。这一分期长期沿用,但也有例外,如2007年出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把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及其《举国皆我敌》一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首诗”,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始自20世纪初。这一变动从“古今文学演变”的观念出发,意谓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更强调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诗界革命”与《举国皆我敌》皆非一蹴而就,而是中国文学长期累积的结果。虽然“五四”新文学进入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新阶段,然而与其说是受了西方影响的结果,毋宁说是在本土思想与文学的基础上取得的进展。
2013年,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出版,在王德威执笔的下卷第六章中,同样强调传统与现代不可分割,而走得更远,把1841—1937年确定为“现代”,且含有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本书不将‘现代性’的开端设置于‘五四’时期,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进程中。”后来在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个“更长的进程”朝过去延展,长度超乎想象。第一篇是李奭学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指出在1635年杨廷筠的宣扬天主教的小册子《代疑续编》中,“文学”一词相当于英语“literature”,使中国诗文、史传等含有新的意涵。其时正值晚明时期,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和凌濛初等人掀起文学狂飙,对后世带来深刻影响。杨廷筠之后传教士将西方文学引进中国,造成“‘文学’的中西范式在十七至二十世纪间递嬗不息”的景观。在这样传统文学的延绵线上“现代性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契机。王德威在《导论》中说:“‘西方’‘现代性’也具有多层意义,不能简化为单一现象。五四作家当然开启一系列对世界、国家、社会、个人的现代想象,为晚清或更早世代的维新文人所不及。但五四时期的现代性话语也可能遮蔽、甚至消解了清末以来诸多实验的可能性,在不同的时空里,这些可能性未尝不指向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潜在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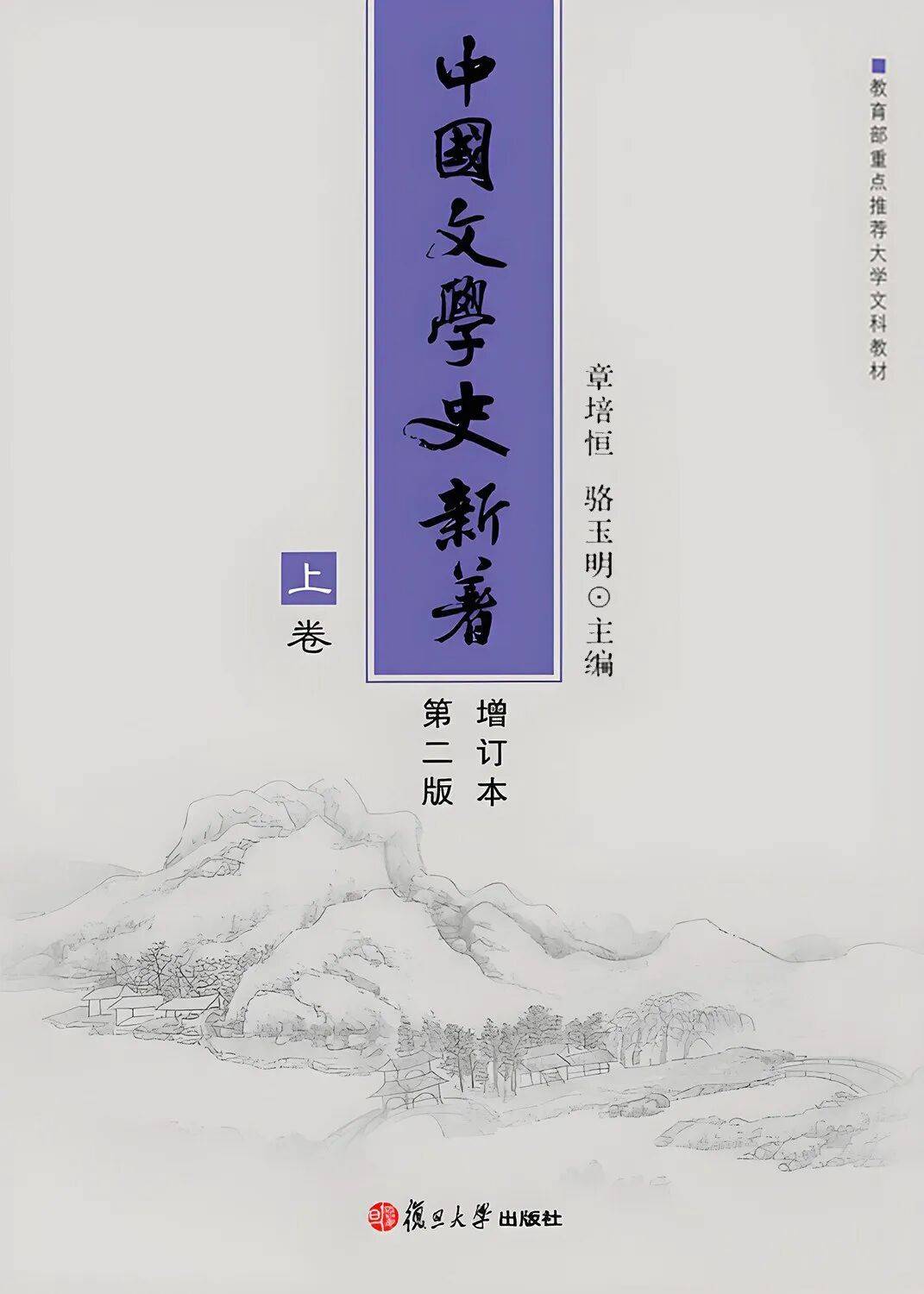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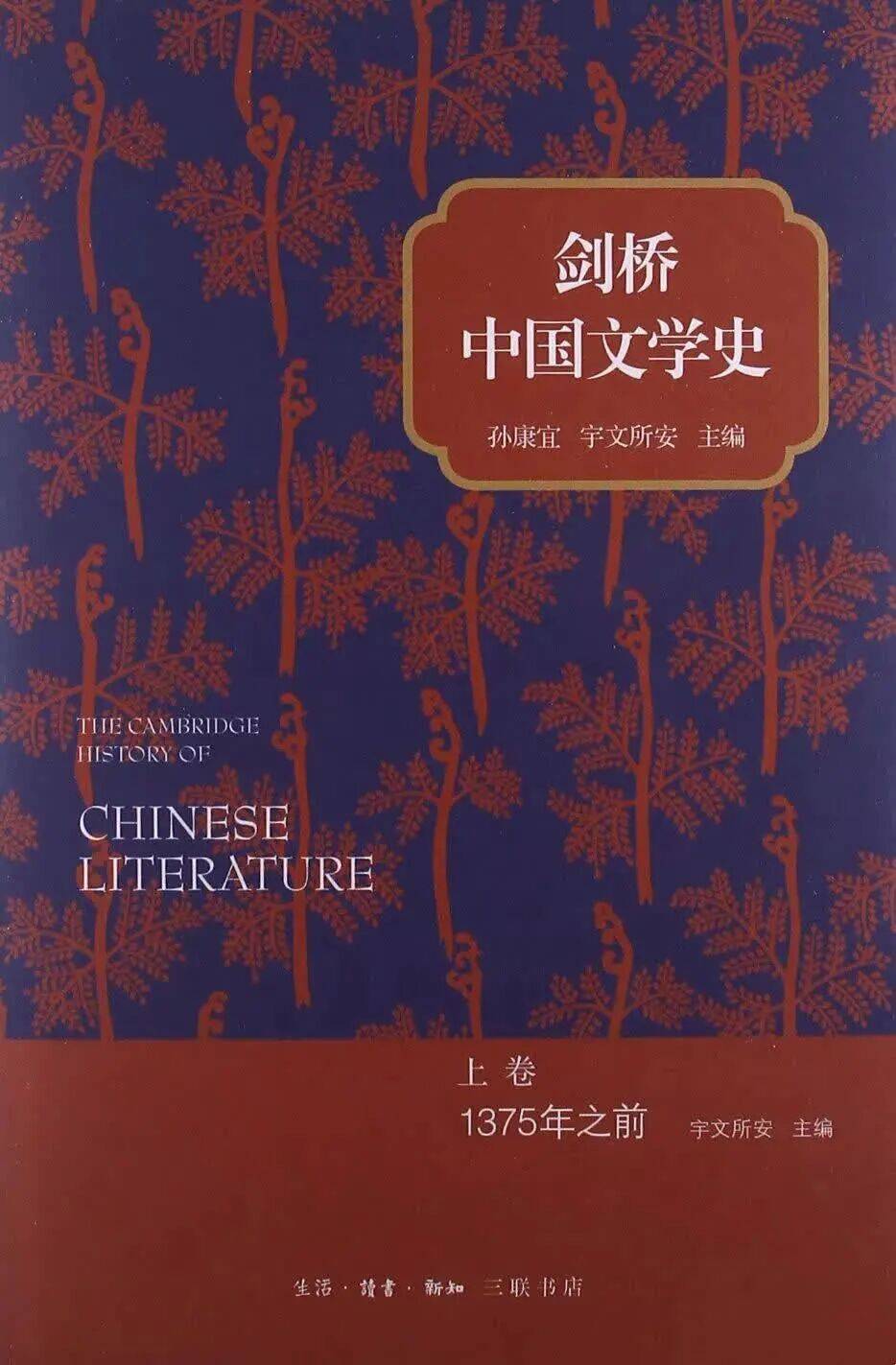
周瘦鹃的中篇小说《红颜知己》正是一个具有“诸多实验的可能性”而被“五四”现代性话语“遮蔽”的例子。周瘦鹃作为“鸳鸯蝴蝶派”自然不受“五四”作家待见,然《红颜知己》却用白线月出版时,《新青年》上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还是文言;它也比“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早了一年。这也不是周瘦鹃第一次用白线年在《小说月报》发表的《爱之花》就是个白话剧本。清末就有人提倡白线年创刊的《杭州白话报》专刊白话小说,限于通俗演义的表述。周瘦鹃一边翻译一边创作,大多用文言,有时也用白线年代白话成为主流文学语言后,周瘦鹃仍是文白兼用,那是更灵活多样的。
发表《爱之花》的同一年,周瘦鹃也发表了文言小说《落花怨》,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其时才17岁,便展露语言天赋。前者模拟法兰西浪漫剧,描写将军夫人爱上年轻子爵,将军派遣子爵上战场,子爵战死,将军把他的心做成羹汤给夫人吃,夫人自杀,魂魄追随爱人而去。后者是留学生故事,写黄女士在伦敦留学,与英国青年坠入情网,婚后遭到婆婆和周围人的种族歧视,最后悬梁自尽,留下遗书,呼吁国人毋重蹈犹太、波兰覆辙而沦为奴隶。这两篇作品风格迥异,皆深刻同情女性的爱情痛苦,再现传统“为情而死”的模式,也建立了他的不无阴郁诡异的“哀情”风格。周瘦鹃后来作为《礼拜六》周刊的编辑之一,几乎每期有其作品,塑造了众多可歌可泣的女性形象,伤感而煽情。他描写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或新式小家庭中女性的屈辱和悲惨,包括时常掺入他的与“紫罗兰”的初恋“影事”,因阶级、种族观念的阻碍而导致梦想的破灭,皆具“高尚纯粹”之爱的规训意味。
《红颜知己》一变“哀情”品牌,是个爱情喜剧。对于周瘦鹃来说,1917年这一年喜事接二连三,他与胡凤英结婚,多半为了筹钱,翻译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被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誉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小说里的男主钱一尘是杭州著名小说家,立志要和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大文豪齐名,写了一部题为《雁影》的长篇小说,去上海找出版,一再遭到拒绝,钱花光不能回家,半夜里游荡在黄浦江边,邂逅一位女子,原来是他的粉丝,她得知事情原委,赠送他一枚胸针,他把它典当换钱,得以坐火车回家。回家向老父小妹诉苦,见到一封信,是北京某出版商愿出版小说,并付3000元稿费。小说出版后,一尘名满天下,老想起那晚的“侠女”,不知其姓名,于是写了《秋水伊人》的小说,刊登在报纸上,隐含寻人之意,果然得到名叫崔明华的女子回应,她来拜访,两人成为朋友,最后在两家家长的同意下喜结良缘。小说一开始是一大段景色描写:
那一抹惨红的残阳,已在两点钟前和大地告了别,半空中便笼着个大黑幕,仿佛向人说,这一天的活剧已告终咧。接着不知道从甚么天尽头地角里刮来一阵排山倒海的大风,龙吟虎啸似的豁喇喇掠过,也不知道向甚么天尽头地角里刮去。天上黑云乱飞,片片衔接,好似无数魔鬼,在那里互相追逐。云罅间嵌着一丸凄冷无光钱儿般大的月儿,忽明忽暗若隐若现的闪动着。虽说有月,简直也等于无月,像这种光景,似乎已近了世界末日。然而那小说家钱一尘氏目前的处境,也正好像这天晦地冥风凄月苦的一夜……
中国小说从无如此开头,这段描写娴熟地、文学性地运用白话,以景色象征主人公的凄惨心境,是极富原创的。像“云罅间嵌着一丸凄冷无光钱儿般大的月儿”是一种新的句式与修辞,相当西化,与周瘦鹃的翻译实践有关。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收入50篇翻译小说,其中英国汤麦斯·哈苔(今译托马斯·哈代)的《回首》的开头:“话说一天正是个阴郁寒冷的耶稣圣诞节前一天,天上满腾着片片彤云,黑压压的不透一丝天光;地上积雪,足有好几寸厚,好似铺着一条挺大的鹅毛毯子。这时已近黄昏,那一天夜色,却愈腾愈密,愈密愈黑,恰和这满地琼瑶,做了个反比例。那泊洛斯班旅馆半新的屋子,孤立在英国一个最美的山谷边上,瞧去又荒凉又寂寞。”这篇翻译同样运用白话。《红颜知己》的这一段之后以占全书四分之一强的篇幅倒叙交代钱一尘的来历,然后回到开头那个夜里,也是大胆的尝试。与此相似的是后来1920年代末,茅盾在《虹》中开头描写梅女士乘轮船经过巫峡,接着以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倒叙了她在四川时期的成长经历。
《红颜知己》实验性极强,显然周瘦鹃成家立业,踌躇满志,便产生表达幸运的冲动,改变“哀情”戏路,套上喜剧的面具,在不确定中绽放激情。小说采用第三人称,而叙事者的视点与口吻始终贴近男主,跟作者的成长经历相符,却通过梦幻和想象表达了一个小说家对成名与爱情的狂想,因此也是一篇奇幻类型的心理小说。它反映了清末民初文学市场的历史形成,而“红颜知己”作为理想伴侣,从传统的男窥对象转变为现代知识女性,又塑造成电影银幕的明星,体现了民初女权观念的兴起与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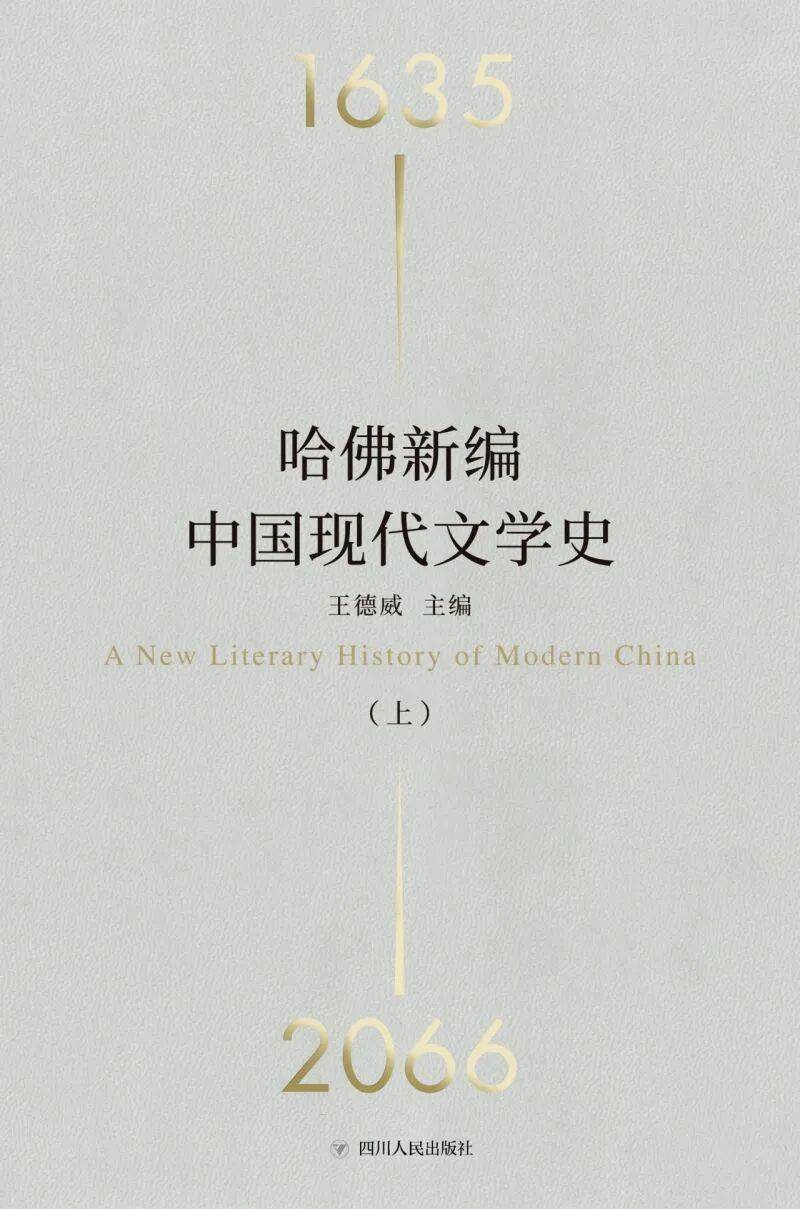

王德威指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公认‘开端’的1919年五四那一天,又到底发生了什么?贺麦晓教授告诉我们,新文学之父鲁迅或其他启蒙精英当天并未立即感受到‘历史性’意义,反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率先反应。”的确,《红颜知己》可说是一个“率先反应”的佳例,其“历史性”在于:小说反映了现代文学市场的历史形成,在钱一尘身上体现了文学的独立与自尊的意识,并创造了引领现代时尚的新女性形象。最富启示的是,小说体现了中国作家获得世界性荣誉的梦想。当他最初看到自己的小说刊登在报纸上的时候,就幻想将来像那些外国文豪们名扬天下:
大家心中嵌着吾的名儿,天天忙着看吾的小说,这是大丈夫何等荣耀的事,以后吾何不就借重那毛锥子,索性做这小说家的生活,将来怕不像那法兰西的嚣俄、美利坚的欧文、德意志的贵推、英吉利的狄更司、俄罗斯的託尔斯泰,名满天下,做那文学界的雄狮么?一尘越想越得意,瞧了那小说,也越发可爱。
嚣俄即雨果,贵推即歌德。其中欧文是周瘦鹃的偏爱,其他都是迄今公认的经典作家,当时能对西方文学有这样的了解,可说是凤毛麟角。钱一尘有了“名满天下”的美滋滋的想法之后,一发不可收,写了长篇《雁影》,果然不同凡响,出版后风靡一时,一位久居中土的美国老博士,是教会学堂的教授,看到《雁影》便大为叹赏,“说不道中国竟有这么一个大小说家,做成这么一部大著作,虽不敢说是东方欧文、东方嚣俄,也能当得上说是个东方马克吐温、东方柯南道尔”,他“为昌明世界文学起见”,费了半年工夫把它翻译出来,“于是半年以后,钱一尘的大名居然跳过了浩浩茫茫的太平洋,诞登西土了。更隔了半年,连伦敦、巴黎市上也有了这《雁影》的译本,委实好算得一部震烁世界的杰作,任那赫赫有名的《红楼梦》也要对之失色。”
小说对钱一尘的狂想及其梦想成真的描写,带有喜剧性夸张,或许让今天的读者觉得天真、滑稽,却表达出一种民族自信,值得由衷赞赏,其实今天来看何尝不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梦想?这对周瘦鹃也很自然,作为南社成员,骨子里有一种“国粹”精神,《礼拜六》也体现了这一点,杂志的编辑王钝根和陈蝶仙等都是南社社员,文化上亦中亦西,如第2期上刊出两页照片,分别是女作家吕璧城和狄更斯,第38期的两页照片分别是杂志编辑同人和英法作家哈葛德、柯南·道尔、莫泊桑和大仲马,如此安排不能说完全无意。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学作家推倒中国文学传统而另起炉灶,与世界文学接轨,如1920年代初茅盾大力提倡法国自然主义,他说:“现代文艺都不免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那么,就文学进化的通则而言,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亦是免不得要经过这一步的。”抱着这样的“进化”观念,文学上难免亦步亦趋,反而阻抑了原始的天真与激情。
钱一尘成为一个小说名家的发迹史,反映了清末以来小说成为救国启蒙的文学主体及其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过程。《红颜知己》的过人之处在于彰显媒介的特殊角色。这基于周瘦鹃的个人经验,六岁时丧父,全家靠母亲做针线活支撑;中学毕业后留校教书,后来辞去教职,以写作为生。他聪敏勤勉,十分多产,收入大增,由是把全家从老城区搬到租界闹市的小洋房居住,他在《礼拜六》上晒出新居照片,书房“紫罗兰盦”颇为精美,这不啻演示了一个文青在短短几年里靠打拼成为都市中产的实例,很有励志意味。在小说里:钱一尘在中学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师,因教书与性格不合而苦恼,于是尝试写小说,投稿即被采用,此后做了职业作家,名声卓著,成为人人皆知的“小说界的明星”。
张灏提出,1895年至1920年代初中国进入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代”,出现了新的传播媒介与新的知识阶层。小说在过去一向是受到儒家正统文学观排斥的“小道”,直至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小说》杂志,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并提倡“小说界革命”,小说成为救亡启蒙的主要文学样式,标志着文学领域的现代转型。此后小说杂志风起云涌,形成了由印刷资本、文学生产、出版、消费所构成的阅读市场,其中稿费制度是个重要环节,使文学写作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职业。《新小说》杂志公布了稿酬标准,创作每千字从四元到一元五角四等,翻译每千字从二元五角到一元二角三等。《红颜知己》里钱一尘辞去教职而陷入经济窘境,“一天早上,正瞧着一张新闻纸,蓦地里发见了一个报馆家征求小说的广告,后边还列着酬赠的等数,一等每千字五元咧,二等三元咧,三等一元咧。那几个三号大字,霍霍的跳进他眼帘去,好像生了口舌,向他朗然说道,这便是你馈贫之粮,你别放过了。”这稿酬标准应当根据《小说月报》,最初周瘦鹃的《爱之花》在该刊发表,得到16元大洋,全家为之欣喜若狂。
小说家一变其低贱身份而受社会尊重,是个进步。梁启超在倡导“小说界革命”时声称在欧洲各国写小说的都是“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这么说意在提升小说的地位。1907年1月《月月小说》杂志刊出吴趼人全身肖像照,向读者拜年,对小说家地位的确立具象征意义。《红颜知己》写道:“那篇小说已在新闻纸上登载出来,一尘见了,直要蹲蹲而舞,瞧那下边署名钱一尘三字,觉得字字都有光彩,料想一纸风行,至少总有个一万份,吾这名儿便也能进一万人的眼儿,二十二行省到处传遍,好不显焕。”这里生动描绘了小说家对于个人荣誉的陶醉,民族“想象共同体”发挥了强大的驱动力。钱一尘“想象中似乎见那各书坊争出重金,上门来买他的稿儿,新闻纸上已登着个空前绝后大著作《雁影》的大广告,那‘钱一尘先生著’六个头号字上边,还加着个当代大小说家的衔头,比了什么公侯伯子男什么虎威将军猫威将军的虚衔,加上几万倍荣耀”。这里形容报纸广告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而“大小说家的衔头”比“公侯伯子男”“加了几万倍荣耀”,认为小说家比王公贵族更为尊显,从观念上经历了现代转型。如1905年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凡事讲究功利实用,向来只有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没有文学与哲学的地位,而“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于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这“美术”在当时也包括文学。又说:“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这为文学带来了独立自尊的意识。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还含有功利目的,后来王国维、黄人、鲁迅和周作人等则主张“纯文学”,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性,在周瘦鹃那里,小说家高于一切,是时代共识的体现。
钱一尘这一人物凝聚着第一代中国现代作家的成长记忆。他的成名过程离不开由资本、作者与受众构成的媒介场域,涉及稿费制度、出版商、广告、读者批评乃至盗版与法律纠纷等环节。周瘦鹃在对文学市场作结构性描写时,含有其感恩之情,虽然他常常自称“文字劳工”,抱怨自己受印刷资本的压榨。正如《雁影》遭到拒绝时,钱一尘愤慨不已:“资本家眼中但有金钱,觉得黄金总比黑字好看……他们心中巴不得一块钱儿,买他一万字,倘能照那买废纸的法儿,称重量,算价钱,一角钱一斤,便再好没有。文人的心血,好比清水,希甚么罕呢?”钱一尘也时时流露其正义感与爱国情怀,像大众一样,对当时的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表示强烈的悲愤与谴责。在那个流落在外滩的晚上,他坐在椅子上,一个印度巡捕不许他坐,说这椅子是外国人坐的,一尘心想:“这上海一隅,明明是吾们中国的地方,如今却被外国人霸占住了,到处都欺侮吾们中国人,那些在朝的肉食诸公,却还争权夺利,闹个不了。即使这大好河山,全个儿进了人家的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他们功名富贵的好梦咧。就是社会上的生活,也何等艰难,国势不振,民生憔悴,连吾们文人也没有噉饭之地,将来怕要陷到那通国皆丐的地步,正未可知呢。”爱国是“礼拜六派”文人的共同立场,尤其是周瘦鹃,在1915年和1919年分别出版了《亡国奴之日记》和《卖国奴之日记》,通过文学虚构对民国军政当局争权夺利、对外卑躬屈膝的行径表示愤怒指斥。
小说家的成功关乎文学市场与社会,而书名“红颜知己”则聚光于一位女性,占据小说舞台的中心。这个成语本身复刻着男性的书写权利,她存在于其视域之中,秀色可餐、善解人意,是天才文人的自我投影。在这部小说里,最后我们知道她叫崔明华。与周瘦鹃惯常描写的悲剧形象不同,她是个知识女性,阳光、善良而聪慧,在杭州读书时喜爱读小说,是钱一尘的粉丝,当她得知自己无限崇拜的小说家陷入困境时,“侠女”般仗义相助,演出了一出美人救英雄的活剧。“红颜知己”不仅指灵魂伴侣,周瘦鹃发明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恋爱“阶级”论。当钱一尘与崔明华相遇,交谈十分投契,不觉间互相以“你”相称,叙述者说:“他们此刻但有知己之感,并没恋爱之心。即使将来免不了这一着,也须在这知己之感的阶级上,酝酿得深了,培养得熟了,才能达到那恋爱之心的阶级。这其间并且还有个阶级,叫做怜惜之意,彼此万不能跳过的。”这反映了民初的恋爱观念,男女自由恋爱,须经过互相了解的阶段,跟以前中国的婚姻制度完全不同。崔明华是一个现代都市“新女性”,从钱一尘的梦幻对象、文学天使到银幕明星,交织着中西爱情文化的混搭色彩,男女角色发生微妙而有趣的换置,意味着传统的男权中心的某种消解,也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文学史上留下有意味的历史性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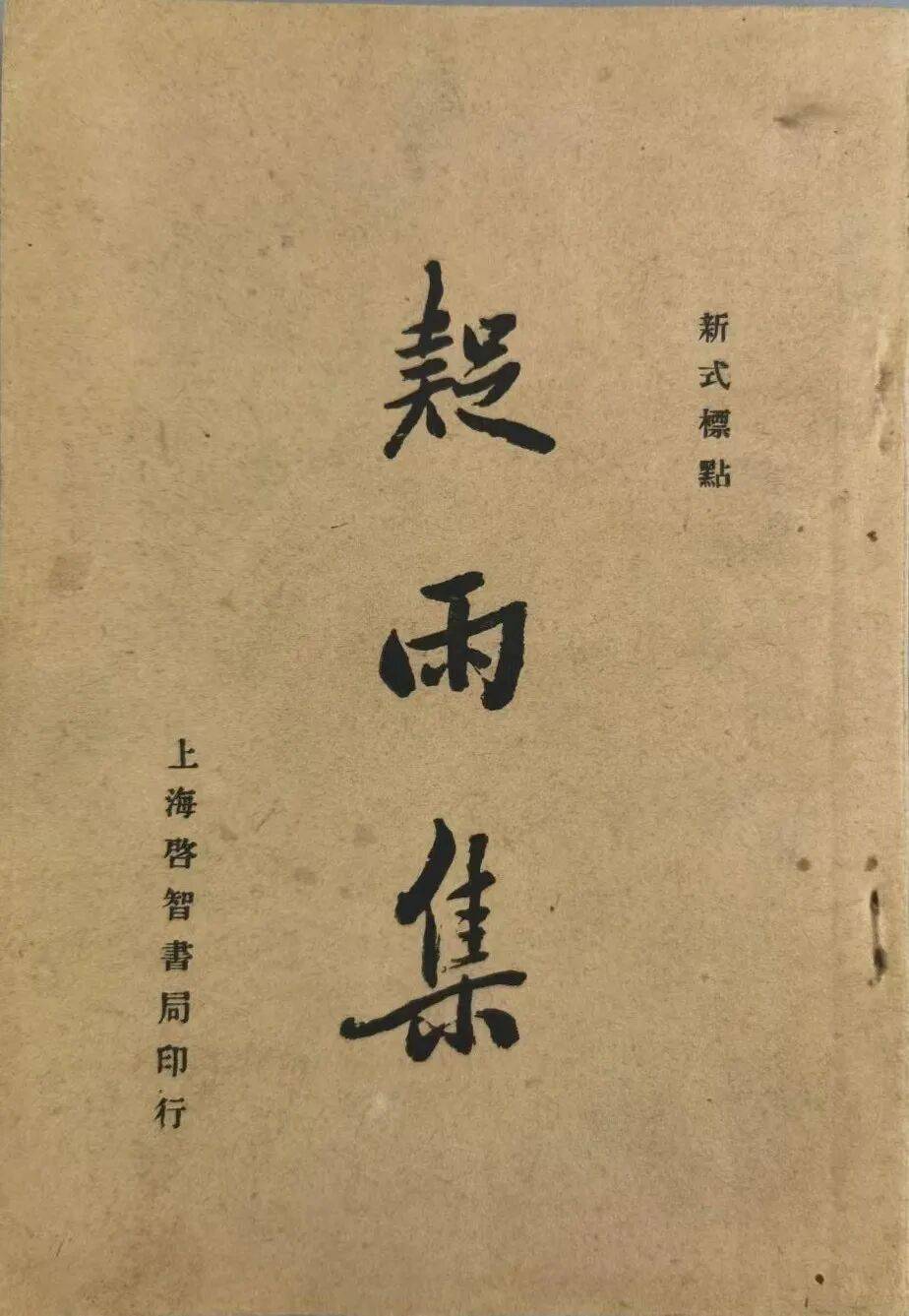

尽管周瘦鹃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但《红颜知己》显示鸳鸯蝴蝶派的本色,具洋派气息。如写到一尘萍水相逢这样的红颜知己,感动得掉下两滴热泪,“这时他们俩原立得很近很近,一尘掉泪时,可巧那女郎正要举手掠他的云鬓,于是这两颗泪珠儿,就不偏不倚的掉在那纤纤玉手之上,女郎冷不防这突如其来的泪珠儿,不觉把手儿一缩,此刻天上倘有月儿,便能照见那香腮上边,晕出两朵彩霞来了。停了会儿,他便半绽樱唇,从一缕暖香馥郁的兰息中,婉婉的带出一句话来道:咦,你,你怎么哭了。”在这样语言表演中,运用“纤纤玉手”“香腮”“樱唇”等来形容,对于受新文学熏染的读者或许会觉得麻麻的。然而从感官文化的角度看,充满视觉、嗅觉和触觉的修辞。当女郎离去,一尘沉醉在她的气息中,想起“美人之贻”:
一尘正发着这种奇想,猛可里却记起手掌里头还握着一件东西,正是那美人之贻。于是闭了眼儿,先把十指反复摩挲着,觉得这东西约摸有两三寸长,着指甚是光滑,中间有一条狭狭的空槽,只能容一个指甲进去,一面似乎镂着甚么花,触处都是芒角;居中又有一个的溜圆的小东西,大约是嵌着一粒珠儿。一尘一时却想不起这是甚么东西,心中便好似蓦地开了爿首饰店,把妇人身上的装饰品,一件件轮数起来;一壁十指乱动,仍摩挲着那东西,末后猛听得卜的一声,忽觉那空槽裂了开来,一头尖尖的,刺得指儿怪痛。到此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东西实是女儿家扣在酥胸上边的胸针,估他价值,总要好几十块钱。……想着,把两手捧住了那胸针,放在嘴上亲了几亲,觉得针上还留着那美人儿酥胸上的余香,宛宛的送进鼻子,沁得心脾都甜。
胸针属于舶来饰品,女子一般佩戴在上衣胸前。“美人之贻”源出《诗经》中《静女》一诗,象征爱的信物。在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里胸针称“别针”,别在旗袍领子中间,为一对夫妻的感情起关键作用,最后使他们重拾爱情,免于离婚的结局。上述一段钱一尘的触摸“美人之贻”的感受,混杂着惆怅、希冀、刺痛与惊喜,而“美人儿酥胸上的余香,宛宛的送进鼻子,沁得心脾都甜”,描摹钱一尘虚拟的迷醉与痴情,对周瘦鹃来说,这渊源于中国抒情传统的“香艳”文学,如唐代韩偓的“香奁体”和南朝《玉台新咏》的“艳体”,描绘女性闺房生活与男女间的私密情感,表现了对女性的审美体验与男性窥视的隐秘人性,正统儒家一向因其“淫艳”而大加指斥。至晚明王次回被认为是集“香艳”大成者,在他的《疑雨集》中富于女体、头发或闺房的香味的描写,如《灯宵纪事》:“踏雾月街艳步狂,微风一路染衣香,游人暗逐芳尘去,拾得儿家紫佩囊。”翩翩风流的诗人在街头闲逛,一路上被女子的衣香所迷醉,一路追随,拾到一个儿童佩戴的紫色的香囊。这似乎颓废、病态,因此王次回被称为“中国的波德莱尔”,如此表达个人细腻的感性体验,颠覆了温柔敦厚的美学典律而为诗艺开拓新的空间。
女体之香虽是男性的狂想对象,但反过来说明女体的魅力难以抵抗,而香味能沁人心脾,在感官世界中别具冲击力。在清末民初出现王次回热,“香艳”文学与现代性挂钩,《香艳丛书》《香艳杂志》《香艳小品》等丛书和杂志不绝如缕,发掘历史文献与创作齐头并进,一个新特点与民初女权意识的觉醒有关,即对历史上女性创作的发掘。周瘦鹃也趁热打铁,在1914年推出《香艳丛话》,收集古今中外的爱情作品或奇谈珍闻,如苏婉仪的《四时思夫曲》:“盈盈十六字王昌,便觉私心暗属郎;依旧抛人闲处住,问君何事早求凰。……”丈夫婚后去异地读书,把她留在家里,她写诗抱怨,既如此何必要早结婚呢?这样表达个人欲望的女声是向来被压抑的。另一则有关法式浪漫女性:“巴黎有某夫人者,所欢最多,一日忽发奇想,印其所爱者十人肖像于指甲上,以慰相思。歌舞场中,人每见其玉葱纤纤,均意中人小影,影里情郎,面目如画,闻巴黎女界,近已盛行此风云。”在叙述如此放诞风流的女性时,周瘦鹃似乎赞赏有加,这种思想的开放程度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嗅觉文化进入现代,文学表现丰富多样,如郁达夫的《沉沦》中,当男主“经过一条暗暗的夹道的时候,一阵恼人的花粉香气,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种肉的香味,和头发上的香油气息合作了一处,扑上他的鼻孔里来。他立刻觉得头晕起来,眼睛里看见了几颗火星,向后面跌也似的退了几步”。经过民族意识的滤镜,男主对日本女子的香味诱惑中带着罪感,跟传统文人的痴迷心态作了切割。在民国时期“香艳”几乎成为好莱坞爱情影片的标配广告用语。而在茅盾、张资平、施蛰存等人的小说里,嗅觉描写各各不同,含有各种意识形态,汇合成都市欲望的复杂交响。
钱一尘把胸针典当后买了火车票回家,继续展开对这位女郎的狂想,在火车上。女郎是他的粉丝,也是爱的天使:
便把那《雁影》垫在身下,闭了眼儿瞌睡着,向黑甜深处,觅他的乐趣。脚儿刚跨进梦乡,第一就瞧见瑶台第一层上,有一个花容月貌、云裳霞珮的仙女,玉婷婷的立着,自己却长跽在台下碧云之中,抬头望着他;见他掺掺素手,把着一部金籖玉轴的书儿,簿面上俨然是《雁影》两个大字,闪闪的放着明光,似乎摘了满天的星斗缀成,瞧那书法狠像是卫夫人簪花格的真迹。他一面放着那金钟银铎似的娇声,朗朗读着,一面把左边一只大花篮中盛着的无数香花,一朵朵向台下抛来,什么紫罗兰咧、玫瑰花咧、莲馨花咧、梅花咧,都有。读一句,抛一朵,不一会碧云中已香花乱飞,香雾漠濛,把个一尘也几乎葬在香花堆里。只那安琪儿却依旧读着书,抛着花,细听娇声,分明是荒田间惠我胸针的那个美人儿,这样不知道经了多少时候,那安琪儿已把一部《雁影》读完。莺声刚绝,便翩翩的飞下台来,向着了一尘展然一笑,传达出上天下地无限的情愫,接着就有千百只金羽玉啄的仙雁,飞集一起,搭成了个飞行艇,给他们两口儿并肩坐着,电掣般飞去。不到一点钟光景,已把八大行星游遍,却见那八大行星中的人,都在那里读他的《雁影》。一见他到,顿时开了欢迎大会欢迎他,他们俩游倦归来,回到原处。一尘得意得甚么似的,不由得手舞足蹈的欢呼起来道:钱一尘今日登仙矣,呼声绝处,他的好梦也就醒了。
晚清以来有关气球、飞艇的科学知识传播引发了科幻文学的热潮,这一段是其余波冲击的产物。钱一尘继续狂想,这位“侠女”仍然是他的粉丝,但男女角色发生微妙变化。在香艳文学中,男性具有女性化倾向,也是明清以来的文学现象,以贾宝玉为典型。在周瘦鹃的自我时尚化的文学实践中,换置男女性别成为有趣的展演节目。她变成安琪儿,是高高在上的爱神,他却在台下“长跽”——长久地跪坐在小腿上——对她恭敬仰望着。她更能动、更强大,带他去游遍八大行星,由于她的传播,八大行星中人都读他的作品。这想象也是来自现实,民初的众多杂志竭力打造新女性形象,她常被作为,手捧书本或杂志,或在灯下苦读。周瘦鹃把这一形象升华为传播阅读文化的女神,他一向把读者奉为上帝,当然要对她顶礼膜拜了。
《红颜知己》中钱一尘是“小说界的明星”。对于“明星”一词我们习以为常,其发明者正是周瘦鹃。1915年他在《美国影戏中明星曼丽璧华自述之语》一文中即称美国好莱坞女演员玛丽·璧克馥为“明星”。那是从英文电影杂志中的“star”一词翻译过来的。在民初文人中他最早拥抱并推广电影新媒介,1914年看了意大利影片《旁贝城之末日》之后,转述成小说在《礼拜六》上发表。在开头说:“闲话休絮,如今吾这纸上舞台总算已行过了开幕礼,那几个名角也已一一登场,以后须得请看官们架起了眼镜儿,瞧这一出大悲剧咧。”他把小说比作舞台,自己好像是导演,让明星们一一登场,含有语言的表演性。1919年他在《申报》上连载《影戏话》,对欧美早期电影从滑稽、侦探到言情的各类片种,从卓别林到格里菲斯的明星与名导一一介绍和评论,等于是一次世界电影科普,更有意义的是提出“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匙也”。把电影看作与小说一样是大众启蒙的利器,是继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之后的重要发明,事实上《影戏话》对于即将起步的中国电影起了催生的作用。


叶凯蒂在《上海·爱:名妓、洋场才子和娱乐文化(1850 —1910)》一书中认为,在清末上海就出现名为“四大金刚”的“明星”。不过民初的“明星”文化具西化色彩,女性社会身份发生历史性变化。由于“共和”政治提倡“男女平权”,催生自觉的女权意识。1912年,领导女子参政运动的沈佩珍和唐群英在成立大会上大打出手,她们的“扇向宋教仁的耳光”便是标志性事件。在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文艺杂志潮中,一些杂志刊登照片,是晚清以来的做派,但《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等女性杂志,包括新兴的月份牌、百美图等,以知识女性、女学生、贤妻良母作为时尚符号,有意让淡出,似在构建一种更有教养、更体面的女性文化。有意思的是,包天笑采取两手策略,其主编的《妇女时报》刊出大量照片,却无的身影,甚至发表《论娼妓之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文章,展望一种更为健康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在其主编的《小说大观》上大量刊登各地当红的照片,当然这也有不小的读者市场。
同时在演艺领域,1913年发生所谓“癸丑中兴”的新剧运动,针对以往“优伶”的低贱地位,周剑云声称:“演新剧者,何以不名伶人而称新剧家?因其智识程度足以补教育之不及,人格品行可以作国民导师也。”相对于一向由男扮女的新剧舞台,陆续出现女子剧团,当然男角由女子扮演,同时男女同台演出也成为新潮流。
文学中男女易装的传奇故事一向吸睛,梁山伯与祝英台脍炙人口,女作家陈端生的《再生缘》中,女扮男的孟丽君惊世骇俗,也是经典之作。晚清《点石斋画报》里不乏扮成男子而招摇过市的新闻。小说《品花宝鉴》描写清末的北方舞台上盛行男扮旦角,民初上海的新剧也是如此,在戏里戏外、同性或异性之间演出真真假假的恋爱活剧。这些故事反映性别观念的变迁,对儒家伦理及男性中心起挑战作用。民初与女权兴起相一致,以男扮女装为时髦,带游戏性质,意味着男权的自我反讽。这方面《礼拜六》周刊起的头,如1913年《游戏杂志》第一期上刊出的漫画家沈泊尘和新剧家王惜花(男扮女)的“游戏结婚之图”,迎合自由结婚的新潮。或《礼拜六》四十期上《周瘦鹃最近化妆小影》与《寒闺思远图》,皆为女装照。后来1924年周瘦鹃主编的《半月》杂志刊出他(坐着)与丁悚(立着)的合照,皆为女装。稍细看他们的服装,时尚而审美,显然用心装扮。周瘦鹃的高领窄袖的短衫,是模仿清末青楼女的流行式样,像早期旗袍款式。两人均戴假发,头路中分,一袭超长围巾,是我们常见的“五四”青年的模样,说不定是学了他们的。
回到《香艳丛话》,翻开书可看到数十幅照片,如“欧洲历史上双美人”——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和打败拿破仑的英国海军将领奈尔逊的妻子哈密尔顿夫人。或如中西各国男女谈情说爱甚至接吻的照片或丁悚画的插图,顺应当时社会上男女间自由交际、西式结婚的时尚新潮。该书把香艳文学与世界爱情文化融会在一起,提供了一个传统的现代转型的范例。而从多张周瘦鹃的图像来看,则是对他的“小说界的明星”的自我展演。丁悚画的《瘦鹃二十岁小影》,他是西装革履,蝴蝶领结,一副金丝边眼镜,衣袋上别朵花,眉清目秀,脸带抑郁。另有世界三大“作家”——狄更斯、司各特和托尔斯泰的图像,含有自己和他们并起并坐之意。这里预埋了《红颜知己》中钱一尘成为世界文豪的种子。确如王钝根说周瘦鹃:“言情小说专家之名大振,少年男女,几奉之为爱神,女学生怀中,尤多君之小影。”他是新升起的一颗文学明星,拥趸无数。
他在《弁言》中自称:“瘦鹃天涯沦落人也。”一个孤独渴望爱情的人。所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句句为名花写影,字字为美人写照。一句一名花,一字一美人也”。周瘦鹃形容自己以“美人”的艺术美颜为天职,也包括对他自己,玩性别错置的戏码。他和新剧男旦演员凌怜影、陆子美合照,跟过去文人“捧角”不同,含有现代“明星”身份的意涵。令人瞩目的是同一页上两张周瘦鹃自己的女装照片,一张穿中式高领镶边绣花袄衫,下身折叠裙子,头上插一朵花;另一张穿着深色绣花长裙,似西洋贵妇,两手伸至脑后,胸部隐隐隆起。照片旁边的说明写着:
黄崇嘏云:“愿天速变作男儿”。而瘦鹃则不欲为男,愿天速变作女儿。自慨枉为男儿二十年,无声无息,负却好头颅。日向毛锥砚田间讨生活,且复歌离吊梦,不如意事常八九。踞天蹐地,恻恻寡欢,作男儿倦矣。颇欲化身作女儿,倏而为浣纱溪畔之西子,倏而为临邛市上之文君,使大千世界众生悉堕入销魂狱里,一一为吾颠倒,一一为吾死。不强似寂寂作男儿邪?春光老去,落花如梦,小窗枯坐,斗发痴想,因长笑入摄影馆,而有愿天速变作女儿之图。
黄崇嘏是古代女子,自称愿作男子,是重男轻女时代的反映。周瘦鹃翻转黄崇嘏,标榜自己甘愿变为女性,却是时尚之举。他吐槽自己百无聊赖,郁郁寡欢,因此要变成西施、卓文君那样的美女,“使大千世界众生悉堕入销魂狱里,一一为吾颠倒,一一为吾死”。在古代,像西施、卓文君被视为倾国倾城、红颜祸水而遭诅咒,在周瘦鹃笔下转化为现代意义的明星,天下男子为之疯狂,这当然是个文学比喻,自觉认识到媒介的力量,而试图驾驭之,从明星文化的角度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万人迷,离不开媒介的有效传播。事实上《香艳丛话》是周瘦鹃运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将“自我明星化”发挥到极致。
最后我们再来看《红颜知己》,当钱一尘成功之后,心心念念那天夜里救济他的“侠女”,遂使小说进阶至电影,从私密性触觉与嗅觉回到公共性的视觉与听觉,其爱情狂想也臻至高潮:
一尘胡思乱想,想不出个计较来。日间多念,念念中带着那侠美人。夜间多梦,梦梦中也带着那侠美人。有时搁笔,只消把眼儿一闭,脑儿里就立刻作怪起来。霎时影戏开场了,那在上海所经的一切事,好似都摄成了影戏片,一张张连续的演着,末后便演到那荒田中的事。电力既足,片子自然也清楚。当时原在黑夜,没有瞧见那美人儿的芳容。不知怎样,这影片中却现出个月明花艳的绝世美人来。珠香玉笑,栩栩欲活。赠针一段,益发做得生动。加着这影戏,并不是寻常的影戏,且还是哀迭生发明的有声影戏。一壁摇着影戏机,一壁又开着留声机,眼儿注在那雪白的布幕上,耳中还听得一串珠圆玉润,莺娇燕脆的妙声,委实和那夜所听得的一模一样,并没一丝变动。
从电影史的媒介考古角度看,自1895年电影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茶园、剧场到电影院放映的过程,伴随着不同的观影体验。茶园、戏院的环境嘈杂,放映早期侦探片和滑稽片,适合普罗趣味。1908年出现西人开设的“虹口影戏院”,后来又有“维多利亚”“阿波罗”和“夏令配克”等,设备愈趋先进,放映最新欧美的故事片或艺术片。虽然票价昂贵,周瘦鹃常去,在看“WAITING”一片时:“不意华灯灭时,触目偏多哀情之剧,笑风中辄带泪雨,伤心之人益觉荡气回肠,低徊欲绝。”黑暗中专心致志地观赏而产生一种沉浸式效果,个人情绪与剧中合而为一,他用“荡气回肠”来形容新鲜的百转千回的视觉感官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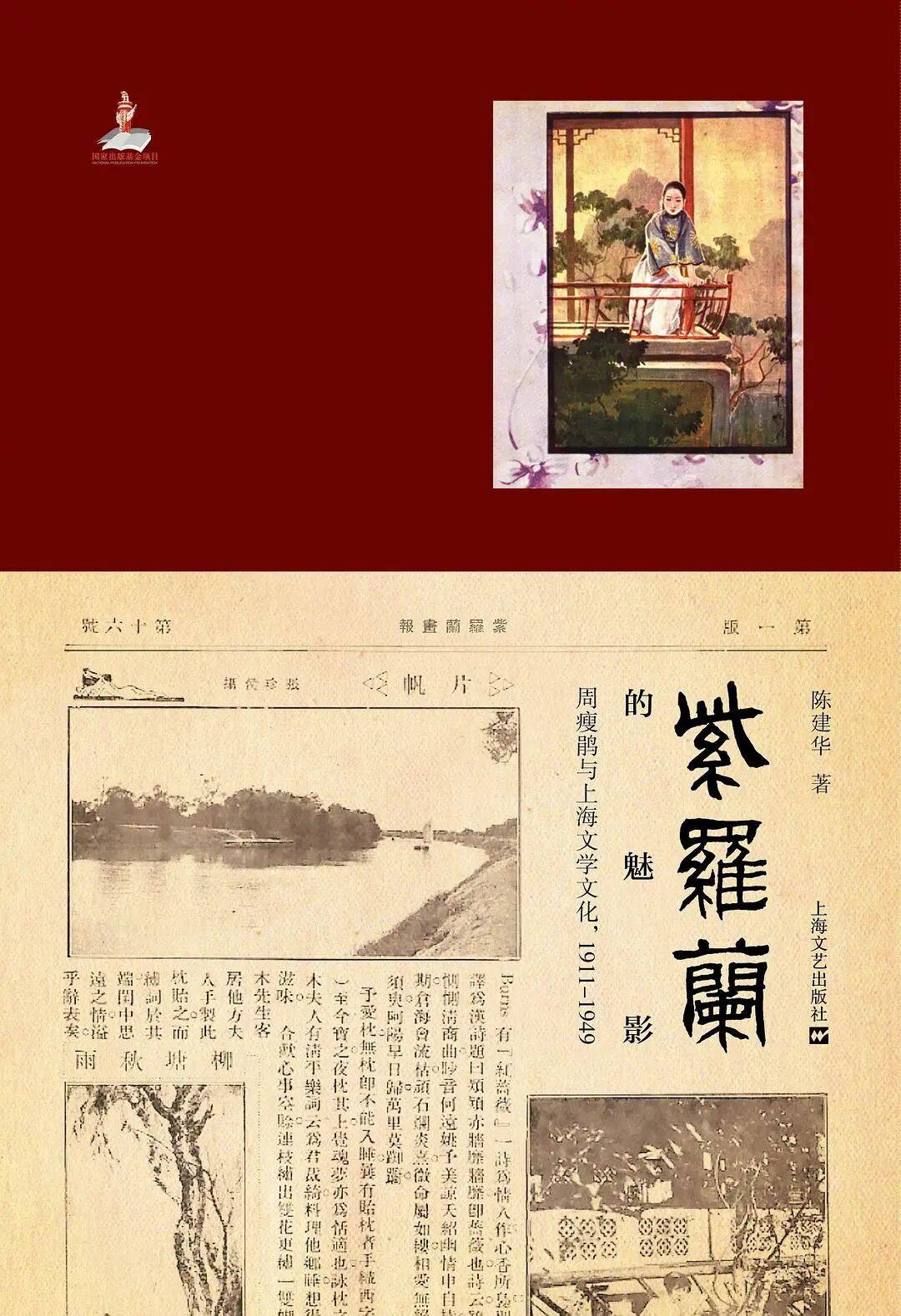
在钱一尘的“脑儿”里“霎时影戏开场”,表现了周瘦鹃对电影的想象性接受,更是一种主体的代入,说明他对电影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阶的地步。这含有三层意涵。其一,晚清时期传教士输入了解剖学上的“脑”的知识,更以电力比作人脑思维的强大功能,周瘦鹃把电影与脑子相联系,从认知的哲学角度看,比王阳明“心学”或康德的外物为心之“显像”、与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把电影和脑神经的视觉机器有相通之处。其二,钱一尘脑中的电影包括拍摄、放映和接受过程,对电影媒介的观念认知在当时颇为超前。其三,原先钱一尘在黑暗中看不清女子的“芳容”,而“电力既足”使“绝世美人”清晰出现在银幕上,这好似在放映现场,其实拍摄过程中经过布光操纵才达到如此清晰效果,换言之,钱一尘好似在自编自导这部电影;所谓“哀迭生发明”的有声影戏,其实是1913年上海的电影院用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为影片配音,这也是周瘦鹃对未来有声电影的想象。
这个插曲标志着对国人对电影媒介的结构性机制、主体意识形成较成熟的电影观念,对国产电影来说是个乐观的预兆,果然四年后突发性产生《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三部故事片,国产电影工业由此启程。这一插曲也表明电影对周瘦鹃所产生的巨大效应。首先,电影给人们带来新的世界认知和视觉冲击,民初的上海各家电影院放映了大量世界新闻片和故事片,所以周瘦鹃说:“于银幕之上,见世界之大,亦弥足以旷心而怡神也。”这跟小说中钱一尘的世界文学的想象不无关系。周瘦鹃充分认识到电影对大众的强大传播功能,并创造性地运用到他的文学生产领域。如这插曲所示,钱一尘作为文学生产者,“绝世美人”作为生产对象,犹如银幕明星,而“电力”涉及如何运用技术手段把明星打造成大众膜拜的偶像。若从周瘦鹃的创作实践看,深受电影的影响,将“自我时尚化”或“自我明星化”,把生产者及其对象熔于一炉,给民初的都市大众文化及媒介领域带来炫目的景观。
在这电影想象的过程里,“赠针一段,益发做得生动”。胸针这一关键道具牵涉男女角色的微妙移置,从个人感官体验的对象转化为文学天使,到代表新女性的美人形象而投影于脑中的电影银幕上,男女主客体在私密与公共空间之间移动,而通过电影技术把美人打造成电影明星。她是钱一尘狂想欲望的对象,却在文学与电影的切换之际完成男女明星角色的换置,正像周瘦鹃在翻译玛丽·璧克馥的文章时,“明星”蕴含着巨大潜力及其他的愿景,继之以他在推进国产电影产业、世界明星文化和女权政治等方面的实践。
在推进中国明星制度的建立方面,周瘦鹃也是个先驱者。1922年但杜宇导演的影片《海誓》开映,在此第一部国产“爱情片”中殷明珠饰演女主角,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而在前一年周瘦鹃在自己创办的《半月》杂志上为殷明珠造势,连续数期刊出文章与照片,甚至报道她穿的皮鞋或使用的明信片,为有关商家做广告,完全是模仿好莱坞卓别林的做派,也是最早打造中国明星文化的一次实践。
《红颜知己》是个多种面向、主题复杂的文本。王德威在描述1841—1937年间文学领域的变化时指出:
这一段时期内,文学之孕育、实践、传播和评价同样产生了绝大变化。舶来的印刷技术、全新的市场策略、识字率的增长、阅读群体的扩大、各式媒介和翻译的繁荣,以及职业作家的出现,共同开创了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新局面。以上情形在前数十年间均是闻所未闻。伴随于此,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观念、学问规化以及文化机构——在经历了激烈的角逐形构之后,最终形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文学的转型确实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显著的现象之一。
这一段概括了晚清以来“文学”所经历的从媒介实践到审美观念的现代化过程。而在《红颜知己》中,通过钱一尘的狂想,这一现代化过程在民国初年已基本完成,沉淀在他的感恩的记忆中。在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米列娜指出“清末民初”的文学被大大低估,它“对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认为民初的“新一代中国作家明确抛弃了充当天地代言人的传统角色,反而如同欧洲的象征主义者或是美国的意象派作家那样,化身为他们想象之宇宙世界的缔造者,对西式以求表达作者心志与情感”。《红颜知己》可印证这一论断,然而不限于都市大众文学市场的成形,更在于文学本身在观念与实践方面所取得的现代化进展。形式上小说具白话的开创性,其修辞、意象与描写手法受到外来的影响,明确含有参与世界文学的宏愿。钱一尘是个生活在具体时空中的小说家,具有爱国与民族意识,而小说从他的个人的情感与幻想、他的喜悦与愤慨,带有民初私小说的新类型,那种登顶世界文学的狂想,体现了对文学、小说家和民族文学的强烈自尊与自信。有趣的是,在其科幻想象的宇宙中,心中的美人成为天使,在八大行星间传播文学的福音,他自己跪坐在她的石榴裙下。在向来由男性主宰的文学创作中不啻是一个性别错位的变动,也是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进步。

梅维恒 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马小悟、张治、刘文楠 译,新星出版社,2016
相对于王德威所概括的文学市场,《红颜知己》更显示从文学朝电影方向的延伸,如周瘦鹃在电影文化方面实践所示,小说不啻预言了1920年代由好莱坞与国产电影——包括男女明星的饭圈文化——所形成的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新景观。这也是王德威所说的“在一个更长的进程中”考察近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好处,能避免碎片化的局限而更具一种整体视野,更利于认识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连续与新变。《红颜知己》仿佛是个人文记忆的容器,储存了19世纪以来照相、石印、电影等新媒介所带来世界文明的成果的累积,而其香艳文学的谱系源远流长,促使我们回望更久远的传统的生命;在民国期间它又延绵不绝,有关“名花美人”的文艺产品承载着现代性价值,不断为都市文化倾注多巴胺活力。
周瘦鹃是个多产作家,骑墙于商业与艺术、有意与无意之间,质量上鱼龙混杂,风格多样复杂,快餐式作品混杂着感性、直觉和潜意识,不乏幽暗、颓废的成分,折射出时代的碎片镜像、作者思想与人格的矛盾。《红颜知己》就是个例子,表面上庆祝新婚,却是遵从母命而与胡凤英结婚,念念不忘其初恋女友紫罗兰,因此寻求艺术慰藉而诉诸浪漫狂想,创造出一个灵魂伴侣,也使作品具有更为深广的意涵。前几年这篇小说被译成英文,然而正如所有堪称经典的作品一样,必须经受阅读的检验与时间的淘洗。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虽然以前已经不止一次地写到过,不久前从媒介考古的角度做了重新解读,但是此后又受到感官研究的刺激,甚至重新思考电影史的“白话现代主义”的议题。尽管结论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对既有结论——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觉得不满足而进行不断反思和探索,我想是对待学术研究的应有态度。◇◆